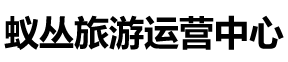路勁基建引爆湖北司法“謎局”
【小編語錄】一宗看似簡單的合同糾紛案件,為何使當地律師感到“莫名其妙”、“很蹊蹺”,竟使一家港股上市公司用“逃離”的方式來抗爭?這起發生在湖北省的案件難道別有隱情?
本刊記者 王亮/文
這是一起在多位湖北當地律師看來“很簡單,并不復雜”的購房合同糾紛案件,但在判決書公布后,律師卻只是隱晦地用“莫名其妙”、“蹊蹺”等觀點一語帶過,不愿多談。
事情緣起路勁基建(01098.HK)旗下管理的荊州市順馳水藍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順馳公司”)與中博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中博公司”)為合作開發荊州順馳太陽城六期項目,在2008年1月18日雙方簽訂的《合作開發合同》,作為該項目施工總承包單位的中博公司于2008年2月19日委托其公司的王子慶負責該項目建設工作。
2012年,荊州市人士黃正昕向湖北省荊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下稱“荊州市中院”)起訴順馳公司稱,其與被告順馳公司于2010年5月14日、6月8日、7月15日簽訂了兩份《商品房買賣合同》和一份《荊州順馳太陽城六期世紀新城車庫買賣合同》(下稱《車庫買賣合同》),約定將順馳太陽城六期項目中的80套(間)車庫及總建筑面積共4500平方米的商品房賣給黃正昕。合同簽訂后,原告依約支付了購房款共計1500萬元,但被告順馳公司收到原告的購房款后卻又與他人簽訂購房合同,將涉案房產(“6487合同”、“6491合同”中的標的房屋)另賣他人。
為此,黃正昕以順馳公司收到其購房款后又將涉案房產賣給他人,損害其合法利益為由,向荊州市中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
1.被告返還原告購房款1500萬元;
2.被告賠償原告損失1000萬元;
3.由被告承擔本案訴訟費。
路勁基建法務人員在回應《證券市場周刊》記者的采訪時表示,“我們本來都不知道這個(購房合同)事情,是在黃正昕起訴后才知道。”在路勁基建看來,這個起訴來得很突然。
順馳公司一方辯稱:
1.黃正昕所持有的合同中凡蓋有順馳公司名稱的印章,都不是順馳公司正在使用的印章,書證中加蓋的該印章均為偽造;
2.順馳公司從未收到黃正昕支付的1500萬元,也從未委托黃正昕將1500萬元支付給其他單位和個人等等。“順馳公司與原告之間未形成買賣關系,原告訴訟請求不能成立,請人民法院予以駁回。”
近四年間,雙方先后經歷了荊州市中院一審、一審重審、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下稱“湖北省高院”)二審、二審重審4次“訴訟戰”,其中順馳公司除了在一審勝訴外,在后三場訴訟戰中均以敗訴告終。
“現在黃正昕在申請執行,查封了我們的三十多套房產了。我們現在正在推動最高院提審,這個事情的最終結局只能是我們‘逃離’湖北省,唯一的方法就是最高院提審。”順馳公司員工如此說道。
這宗看似“很簡單,并不復雜”的合同糾紛案件,為何使當地律師感到“莫名其妙”、“很蹊蹺”,竟使一家港股上市公司用“逃離”的方式來抗爭?這起發生在湖北省的案件難道別有隱情?
上篇:
蹊蹺的“雙面”判決
在荊州市中院一審時,黃正昕為支持其主張向荊州市中院提交了20個證據:第一組證據包括編號為“6487”、“6491”的《商品房買賣合同》和《車庫買賣合同》,用于證明順馳公司將開發的太陽城六期項目中的80套(間)車庫及總建筑面積共4500平方米的商品房賣給黃正昕;第二組證據包括《委托書》、2010年5月20日和6月8日的《付款委托書》、《中國農業銀行個人結算業務申請書》三份、《荊州市商業銀行進賬單》兩份以及加蓋有中博建設集團有限公司荊州分公司(下稱“中博荊州分公司”)財務專用章的《收款收據》六份等,用于證明黃正昕已依約將購房款1500萬元匯至中博荊州分公司賬戶;第三組證據為荊州房產信息網信息截圖兩份,用于證明順馳公司將涉案房屋(除車庫外)另賣他人;第四組證據為《土地使用證》、《湖北省商品房預售許可證》等五證,用于證明上述五證曾懸掛于被告設在太陽城六期項目地點的售樓處;第五組證據為《順馳土地款科目往來款明細賬》,用于證明中博荊州分公司已將購房款5141萬元在內的5900萬元支付給順馳公司;第六組證據為視頻錄像光盤一張,用于證明原告購房時所接觸的售樓人員仍在順馳公司任職;第七組證據為買受人陸光遠的《商品房買賣合同》,用于證明該合同的印章加蓋情況及付款情況與原告編號為“6487”、“6491”的《商品房買賣合同》及《車庫買賣合同》相同。
在庭審質證中,順馳公司對黃正昕所舉證據均有異議。順馳公司表示:黃正昕提供的《購房買賣合同》以及《付款委托書》加蓋的印章印文均不是順馳公司的真實印章加蓋,并申請對合同中加蓋印章的真實性進行司法鑒定;而且,順馳公司并未收取黃正昕支付的所謂“購房款”,中博荊州分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據與順馳公司無關,黃正昕一方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已向荊州順馳支付了所謂的“購房款”;對于第七組證據,荊州順馳認為該合同也屬假合同,陸光遠已向沙市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
順馳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證據主要有:王子慶書寫的《情況說明》(后文會有詳述)以及中國農業銀行存款、取款業務回單各一份和中國建設銀行轉賬憑條一份,用于證明黃正昕所持有的三份合同加蓋的印章為王子慶私刻,王子慶仍分期向黃正昕還款,其與王子慶之間屬于民間借貸關系;西南政法大學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鑒定意見書》,用于證明黃正昕出具的三份購房合同以及委托書中出現的印文并非荊州順馳的公章所加蓋。
對此,黃正昕辯稱,所持有的合同均在順馳公司售樓處簽訂,順馳公司沒有在售樓處公示相關情況,原告作為普通購房人不可能知曉被告所稱的購房流程;被告在其他地方也使用過合同上使用的印章,但原告無法從有關機關獲取相關證據;原告認為因王子慶未出庭,被告不能將其所寫的情況說明作為證據使用。
《湖北省荊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下稱“一審判決書”)顯示,(荊州市中院)另查明:“6487”合同和“6491”合同、《車庫買賣合同》以及委托書、兩份付款委托書上加蓋的刻有被告公司名稱的公章印文經西南政法大學司法鑒定中心鑒定,并非順馳公司的公章蓋印形成。
荊州市中院認為:涉案的“6487”合同和“6491”合同、《車庫買賣合同》的“出賣人”欄加蓋的刻有被告順馳公司名稱的公章印文經鑒定均不是被告的公章蓋印形成,即使“買受人”欄均有原告簽名,但不能認定被告有與原告簽訂上述合同的意思表示,因此原告與被告之間的商品房買賣合同關系不能成立。
在一審中,黃正昕主張,王子慶有權向其銷售涉案房屋,王子慶向其銷售涉案房屋并簽訂的合同對被告具有約束力。
對此,荊州市中院認為,王子慶并非順馳公司的工作人員,順馳公司也未授權王子慶對外銷售房屋并與買受人簽訂相關合同……王子慶作為中博公司委托的涉案項目建設工作負責人也無權與房屋買受人簽訂合同,原告主張王子慶有權向其銷售涉案房屋的理由,不能成立;此外,原告也未能舉證證明被告已收取其支付的1500萬元,原告也未曾要求被告按照三份合同履行交房義務。
“綜上,荊州順馳與黃正昕之間不存在買賣合同關系,王子慶無權向黃正昕銷售涉案房屋,涉案的三份合同對順馳公司均不具有約束力,原告黃正昕主張被告應依合同承擔違約責任,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據此,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駁回原告黃正昕的訴訟請求。”一審審判日期為2012年10月16日,審判長為郭莉。
黃正昕不服,上訴至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后,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原審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發回重審。”
2013年10月15日,荊州市中院開庭進行了審理(下稱“一審重審”)。黃正昕提供的證據在原基礎上增加了《合作開發合同》和《授權委托書》等證據。
荊州市中院于2013年12月27日發布重審判決書,審判長由郭莉變為陳時中,這次荊州市中院的態度有了很大的改變。
首先,對于順馳公司所提供的核心證據之一的王子慶所寫《情況說明書》,荊州市中院以“王子慶未出庭,無法確定其真實性”為由“不予采用”。
荊州市中院認為,應該認定上述三份合同有效,原告黃正昕與被告順馳公司形成商品房買賣合同關系,其理由是:
一、涉案合同簽署地均在順馳公司設立的順馳第六期售樓處,其合同填寫人確實為該項目售樓部的工作人員;
二、在整個簽約過程中,原告已盡到了必要的謹慎注意義務;
三、三份合同的履行情況也完全符合中博公司之前簽訂的《合作開發合同》的相關約定,唯一不同之處在于合同上加蓋的印章有別于順馳公司提供的文件上的印章;但就三份購房合同而言,它本身是客觀真實的,它既表達了原告購房的真實意思,又符合順馳公司和中博集團當時共同委派的售樓處的利益取向;對于合同上的印章與順馳公司當時所用印章不一致的問題,只能表明兩被告對于設立的售樓處疏于管理,而不能因此而否定合同的真實性、有效性;
四、《司法鑒定中心司法鑒定意見書》的鑒定結論只能說明原告合同上加蓋的順馳公司印章與順馳公司提供的印模不是同一的,并不能由此證明原告合同上的順馳公司印章是假的等等。
“被告順馳公司在與原告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后,又將涉案房屋賣給他人,構成違約,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荊州市中院認為,“原告與被告順馳公司之間具有商品房買賣合同關系,被告中博集團應與被告順馳公司共同承擔返還原告購房款及賠償損失的連帶責任。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判決如下: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由被告順馳公司、被告中博集團共同返還原告購房款1500萬元,且共同賠償原告損失1000萬元。”
“同一個法院,出現兩個不同的判決結果。”順馳公司相關負責人對《證券市場周刊》記者表示,“即便中博公司進來了,也許這事和中博有關系,或者沒有,但是和我順馳公司的關系是應該沒有任何變化的。”
順馳公司一審代理律師江律師對《證券市場周刊》記者表示,“對這個案件,我個人認為,黃正昕與順馳公司之間確實沒有形成買賣合同關系,因為在審判的過程中,舉證材料都有記錄,黃正昕從來沒有找過順馳公司,一直以來都是在和中博公司的王子慶之間發生關系。從常理講,開發商是順馳公司,你花1500萬買房子,這也不是一個小數字,又有購房合同,你總得來找順馳公司一次(收房)啊,這是基本常理吧,是不是?”
“我們現在有一個觀點,你有什么證據證明我違約了呢?你就從來沒有找我要過房啊,你有什么證據說我不把房給你?你從來沒有找過我,現在說我違約了,真是莫名其妙。”江律師如此說道。
在上述審判書公布后,順馳公司、中博集團均表示不服,又向湖北省高院提起上訴,但是湖北省高院審理后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實體處理得當,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即便順馳公司此后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湖北省高院審理后仍認為,“黃正昕與順馳公司成立商品房買賣合同關系,三份合同真實有效。”最終“維持湖北省高院原判決。”
江律師表示,“司法裁判權在法院手上,我對這個判決本身是不服的,把案件的實質改變了,我們反復提出的一些問題,這個判決書是沒有解決的。我們現在要求判決書要充分說理,你為什么要這么判,你要把道理說明白,說的充分,但我們認為是不充分的。”
實際上,荊州市中院和湖北省高院都多次在審判書中說,“雙方最核心爭議是順馳公司與黃正昕之間是否形成商品房買賣合同關系。”《證券市場周刊》記者翻閱四次審判書后整理發現,雙方圍繞“是否形成商品房買賣合同關系”爭議的核心分別是黃正昕簽署購房合同時是否盡到了必要的謹慎義務、合同印章真實性、資金去向及性質、證人證言應否采用等。
《證券市場周刊》記者發現,黃正昕方提供的部分證據仍有諸多疑點難以解釋,而荊州市中院以及湖北省高院對雙方提供的證據也有采用“雙重標準”之嫌。
中篇:
爭議焦點之——黃正昕做到必要的謹慎注意義務了嗎?
關于“黃正昕盡到了必要的謹慎注意義務”一說,法院在判決書中的觀點大致如下:黃正昕是在順馳公司售樓處內與王子慶代表的順馳公司簽訂的上述合同,合同上亦加蓋了順馳公司的印章,盡管王子慶不是順馳公司的工作人員,但編號“6487”合同與經荊州市房管局備案的“6223”合同(當事人分別為順馳公司與李世東)是同一人填寫的,證實涉案合同是由售樓處的工作人員填寫。
實際上,在黃正昕上述提供的所有證據中,難尋一條證據能證明其是在順馳公司售樓處內簽署的購房合同。
有意思的是,荊州市中院在一審審判書中提到:“經審理查明:原告與王子慶接洽后分別于2010年5月14日、6月8日、7月15日簽訂了《商品房買賣合同》以及《車庫買賣合同》……”需要注意的是,荊州市中院只是說“黃正昕與王子慶接洽后簽署了購房合同”,并沒有說簽署地點是在順馳公司售樓處內。
而在一審重審中,荊州市中院的陳述變為,“2010年5月14日、6月8日、7月15日,原告在第一被告設立的順馳公司六期項目工地內的售樓部內,與王子慶簽訂了《商品房買賣合同》以及《車庫買賣合同》。”此后在二審、重審等判決書中一直沿用此說法。
順馳公司表示,“她(黃正昕)說是在我們的售樓部(簽署購房合同),其實王子慶也提到是在她的辦公室里邊(簽的)。”
《證券市場周刊》記者拿到一份王子慶書寫并遞交到法院的《情況說明》,落款時間為2014年9月21日,王子慶在文中提到,“我是中博集團荊州順馳太陽城六期項目工程負責人,在該項目還在施工期間,我為了與人合作開發荊州南門一個地產項目,由于該項目需要資金量較多,導致資金緊張,周轉困難,為了南門房地產項目開發的正常運行,后通過朋友介紹認識開小額貸款公司的黃正昕……當時我在向黃正昕借錢時,由于資金量較大,黃正昕要求提供抵押物,于是我就找到順馳公司曾臨時聘請為該公司填寫合同的剛畢業的大學生吳萍(我與吳萍有一種特殊關系,她的父親是我工地的一個包工頭),要她幫忙填寫了兩份商品房買賣合同,另一份車庫合同是我手下的人與黃正昕那邊的人共同寫的,同時我自己刻了一枚順馳公司的章子,幫三份合同蓋好章子后送到黃正昕辦公室二樓簽訂的。”
王子慶還對《證券市場周刊》記者表示,用購房合同做借款擔保是黃正昕提出來的,她說走個過程做個形式,主要就是借錢。
順馳公司還向《證券市場周刊》記者出具了一份簽訂日期為2015年7月2日的《吳萍調查詢問筆錄》,在筆錄中吳萍表示,“6487”合同是我填寫的,“6491”合同不是我寫的,具體(簽約)時間我不記得了,不是在售樓部填的,地點記不清了。“當時他們打電話到我家讓我幫忙填合同,我那時正在籌備婚事,很忙。”
吳萍還說她是2009年5月或6月到售樓處,填寫這份購房合同時不在(順馳公司)了。“我問過他(要她幫忙填合同的人)做什么用,他說不是真的賣房,只是給這個人做貸款抵押。我是一邊填一邊問的,主要是因為幼兒園、活動中心不能賣,我有疑慮。”吳萍在筆錄中如此說道。
當順馳公司代理律師問,“為什么要找你來填寫這份合同?”吳萍也說,因為我爸爸在王子慶那里做事,他們跟我比較熟。吳萍還說,她填寫的這份合同是空白合同,沒有蓋順馳公司的章,也沒有黃正昕的簽名。“我填的合同,落款的兩個時間也都不是我寫的。”
據吳萍介紹,順馳公司與購房客戶簽訂合同的流程是:“客戶先交錢,拿首付款回單到公司會計那里換收據,然后我們才簽合同,然后到房管局備案。”吳萍說,“公司蓋章管得很嚴。”
“交完錢后,黃正昕從來沒有主張過向順馳收房。”順馳公司負責人質疑道。
江律師表示,“退一萬步講,就算你這合同有效,你從來沒找順馳要過房,你把錢付了以后,也沒找順馳開過票,你沒有主張過房子,天下哪有這樣的事兒?1500萬也不是個小數字了。你(指黃正昕)為什么沒來找順馳公司開票?你花1500萬找我買房子,你為什么從來不找我要房子啊?你把這兩個給我解釋清楚,我們都服了。我們不搞(講)法律上的表現代理,法律上面的事太復雜,老百姓也看不懂,我們把復雜的東西,用最簡單的語言,大家都能理解的一種表達方式來討論。”
另外,據了解,上述三份購房合同的“出賣人”欄均加蓋了刻有順馳公司名稱的公章印文,“6487”合同、“6491”合同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欄均為空白,“車庫買賣合同”的“出賣人”欄還填寫了“王子慶”。
順馳公司負責人給《證券市場周刊》記者拿了一份太陽城六期的正式購房合同,最后一頁,出賣人一欄是順馳公司的公章,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人則蓋有順馳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法人章。“所有人,統一版本的購房合同,也就是所謂的真合同。”黃正昕方提供的合同,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人一欄都是空白的。
爭議焦點之——資金去向及性質之謎
王子慶還在《情況說明》中表示,“我于2010年5月開始向黃正昕借款多次,合計1500萬元,約定月息2.8%,從借款后,我支付利息約800萬元,后因我確實無力支付利息后,黃正昕用與我簽訂的三本假《商品房買賣合同》把順馳公司告上了法庭。在整個過程中,順馳公司是不知情的,也是無辜的。”
順馳公司在二審中提交的新證據包括:《審計報告書》一份,擬證明黃正昕不存在真實的購房行為,順馳公司并非黃正昕1500萬元款項的收取人和獲益方。
據湖北五環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審計報告書》(審計日期為2014年5月6日):2008年1月18日,順馳公司與中博集團合作建設順馳太陽城六期,土地面積約為49.78畝;根據合同簽訂,順馳公司不單獨向購房客戶收取房款,所有售房款項均由中博集團收取并向甲方支付,形成往來賬款。“我們對順馳公司2008年1月1日-2014年4月30日期間的其他應付中博往來賬戶及六期銷售合同進行審計,并關注客戶黃正昕的購房合同繳納購房款的情況。”
經湖北五環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確定,自2008年1月1日-2014年4月30日止,順馳公司收到中博集團轉交的1.19億元售房款,該售房款記錄中未見中博公司將黃正昕購房款1500萬元匯入順馳公司賬戶;截至2014年4月30日,順馳公司提供六期銷售合同共517份,金額合計1.48億元。“未見順馳公司與黃正昕客戶簽訂1500萬元購房合同。”
對此,黃正昕提出質疑稱,《審計報告書》是順馳公司委托審計部門所做出的審計,所以報告本身不具有公正性,順馳公司在財務審計中直接將三份購房合同抽走就可以達到審計報告的結論,不排除這種可能性,故該報告不具備公正性和合法性。
湖北省高院亦表示,順馳公司雖提交了一份《審計報告書》,但該審計系順馳公司單方委托所做的鑒定,無法核實鑒定資料的完整性與真實性,黃正昕質證時亦表示不予認可,原判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六條的規定對該《審計報告書》不予認定,并無不當。
事實果真如此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六條規定:“當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實的專門性問題向人民法院申請鑒定。當事人申請鑒定的,由雙方當事人協商確定具備資格的鑒定人;協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當事人未申請鑒定,人民法院對專門性問題認為需要鑒定的,應當委托具備資格的鑒定人進行鑒定。”
“黃正昕沒有提出找第三方審計機構鑒定的要求。”順馳公司負責人如是說。
而黃正昕在一審時提供的第五組證據——《順馳土地款科目往來款明細賬》,用于證明中博荊州分公司已將購房款5141萬元在內的5900萬元支付給順馳公司,也并不能證明其1500萬元購房款最終支付給了順馳公司。
路勁基建法務同時表示,“我們的主張都是能夠提供證據予以支持的,現在等于是(法院)以推理解釋否定了有證據證明的事實。”
更為離奇的,售房款竟然出現了三個版本。
根據審判書,“黃正昕與王子慶接洽后分別于2010年5月14日、6月8日、7月15日簽訂了編號6487、6491的《商品房購房買賣合同》以及一份《車庫買賣合同》,合同價款分別為930萬元、420萬元、400萬元,合計1750萬元。”
此后,王子慶又向黃正昕出具了均加蓋順馳公司名稱公章印文、時間為2010年5月14日的委托書一份,以及時間分別為5月20日、6月8日的兩份付款委托書。委托書要求原告將“6487”合同購房款中的250萬元直接匯入中博荊州分公司賬戶,5月20日的付款委托書要求黃正昕將“6487”合同購房款中的490萬元匯入中博荊州分公司賬戶,剩余的186萬元匯入王子慶個人賬戶,6月8日的付款委托書要求原告將“6491”合同的購房款中356萬元匯入中博荊州分公司賬戶,剩余64萬元匯入王子慶個人賬戶。付款委托書中要求黃正昕付款金額合計為1346萬元,較購房合同金額約定價款少了404萬元。
黃正昕稱,其分別于2010年5月14日、5月21日、6月8日、7月15日向中博荊州分公司賬戶匯款250萬元、350萬元、500萬元和400萬元,共計1500萬元。
為何同樣的購房合同出現三個版本的購房款?荊州市中院、湖北省高院在審判書中都沒有給出進一步解釋。
順馳公司提供的《代理補充意見備忘錄》顯示:2010年5月14日、5月21日、6月8日、7月15-16日王子慶以《領款單》從中博集團荊州分公司領取250萬元、350萬元、500萬元和400萬元,合計1500萬元。《領取單》上“事由”一欄分別記載的是“活動中心房款”、“順馳活動中心房款”、“活動中心幼兒園房款”和“順馳項目”。
順馳公司稱,黃正昕持有的6487號和6491號合同,其標的物是活動中心和幼兒園。
這與黃正昕上述所說“分別于2010年5月14日、5月21日、6月8日、7月15日向中博荊州分公司賬戶匯款250萬元、350萬元、500萬元和400萬元,共計1500萬元”有著驚人的巧合。
順馳公司表示,上述兩個環節構成了出借款項和收取借款完整過程,充分說明,黃正昕匯入中博集團荊州分公司的1500萬元均由王子慶領取,這明顯是個人借款行為。
不過,黃正昕的訴訟代理人辯稱,貨幣為種類物,故以上事實不能證明王子慶領取款項即為黃正昕匯入款項。湖北省高院表示,僅能證明中博公司收到黃正昕支付的1500萬元后,王子慶從中博集團處領走1500萬元,上述情形是中博公司對自有資金的處分,并無證據證明與黃正昕有關聯。
但是,順馳公司在二審期間,還提交了一份還付利息銀行憑證,擬證明王子慶向黃正昕還付1500萬元借款利息,王子慶與黃正昕之間系借款關系,黃正昕不存在真實的購房行為。其中,王子慶在2011年11月8日向鄒明享(黃正昕的丈夫)支付42萬元。
對上述證據,湖北省高院表示,“僅證明王子慶與鄒明享之間的資金往來,因與本案無關聯性,本院不予認定。”
一位要求匿名的荊州律師卻持有不同觀點,“王子慶把錢打到鄒明享賬戶上,這筆錢是干嘛的?法院可以去取證。”
爭議焦點之——“真假”印章
順馳公司還向《證券市場周刊》記者提供了一份西南政法大學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鑒定意見書》,鑒定意見為:合同編號為“6487”、“6491”的《商品房買賣合同》以及《車庫買賣合同》、《委托書》、兩份《付款委托書》上的公章印文與樣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公章蓋印形成。
在一審重審中,荊州市中院表示,《鑒定意見書》的鑒定結論只能說明原告合同上加蓋的順馳印章與順馳公司提供的印模不是同一的,并不能由此證明原告合同上的順馳公司印章是假的。
法律素有“誰主張誰舉證”一說。順馳公司負責人表示,“全荊州你(黃正昕)能找出第二份合同和你這(印)章一樣的嗎?你(黃正昕)能證明這是我們公司的(印)章嗎?”
江律師也表示,我們提出這個章是假的,是有一個司法鑒定,鑒定結果是和順馳公司使用的章是不一樣的,而且這個假章是怎么來的,我們把來源搞明白了,王子慶自己有陳述,這個假章的出處都有了。“但是判決書對印章的表述令人很遺憾。”
在《情況說明》中,王子慶提到,“我自己刻了一枚順馳公司的章子,把三份合同蓋好章子后送到黃正昕辦公室二樓(園林路與江津路交匯處,海皇酒店隔壁)簽訂的。”
根據法律規定,法院判決書網上公開發布,老百姓公開也可以查到。江律師表示,如果把這個上網,若“雖然章子是不同的,但不能證明是一個假章子”這個認定成立,社會秩序就完了,就爛了,比如我現在刻一枚國務院的章子,只要是國務院的工作人員都可以刻一枚這樣的,把章子蓋上去,就是鑒定國務院沒有用過這枚章子,你也不能證明這是個假章子。
“現在不僅是我能證明這不是我的章子,而且我把(假章)源頭都搞清楚了,(法院)還不認定這個是假章子,說這個章子是有效的,我要承擔責任,我就在想,以后要證明這一枚是假章子的話,有什么樣的方式才能夠達到我們法院、法官認定假章子的標準,你給個標準給我。”江律師如是說。
江律師還表示,“你說王子慶他不知道私刻假章的后果嗎?他不曉得這個要坐牢嗎?這個(證言)對他很不利啊。”
據悉,如果最后有證據表明證人提供的證言是虛假的,其也要承擔法律責任。
而王子慶在上述《情況說明》中坦言,“我王子慶雖然干了違法的事情,但是開始我出發點是善意的,造成今天的局面,我為自己的行為感到內疚,目前我只能講出當時實際情況,不能因為我冤枉了無辜,該我承擔的責任我將不遺余力努力承擔,請最高院查明實際情況”。
湖北省高院在二審時還表示,順馳公司并未就其主張王子慶私刻公章向公安機關報案,追究王子慶的相關法律責任,故不能由此證明黃正昕合同上所蓋順馳公司印章為假,進而否認涉案合同的真實有效性。
路勁基建法務負責人質疑稱,“我起不起訴王子慶和認定王子慶私刻公章這個事情沒有關系吧?”
江律師則表示,“我向公安局報案就是假的,沒向公安局報案就是真的?這是什么邏輯?法院應該憑證據來認定真的假的,不是說我向公安局報了案就是假的,不報案就是真的,哪有這個說法呢?法院這個理由我們是難以接受的。”
“那份鑒定報告是權威機構做出來的,不能否認他的這個鑒定報告,如果順馳在房屋買賣中用過這個章,你能證明這個是順馳的章,也可以,但是現在沒有看到這方面的證據。”一位要求匿名的荊州律師如此說道。
爭議焦點之——證人證言“花樣否定”
不難發現,王子慶及吳萍的證人證言對整個案件來說尤為重要。其中,王子慶書寫的《情況說明》尤為關鍵。但是,荊州市中院、湖北省高院在四次審判書中對此竟給出了四種迥異的說法。
在一審時,荊州市中院表示,“雖王子慶本人未出庭,但結合本案其他證據及庭審調查,對該《情況說明》中所陳述的與本案具有關聯性事實經過,予以采信。”
可在一審重審中,荊州市中院卻又說,“因王子慶未出庭,無法確定其真實性,不能做本案的證據采用。”
同一法院,為何對同一證據采取截然相反的觀點?
在二審中,順馳公司、中博公司申請證人王子慶出庭作證,王子慶陳述稱:由于當時做太陽城項目沒有錢了,所以就向黃正昕借款1500萬元,約定利息是兩分八,其支付了七八個月的利息,本金和剩余的利息均沒有支付,簽訂假購房合同就是為了借款作為擔保。
此時,湖北省高院又表示,“(上述陳述)僅有王子慶的陳述而無其他有效證據證明,本院不予認定。”
而在二審重審時,湖北省高院再度改口稱,“王子慶是中博公司工作人員,與本案有利害關系,其證言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對于上述“利害關系”一說,江律師表示,“我們的規則是,當事人作出對自己不利的陳述,(法院)要認定;當事人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而且排除其他人責任的陳述,可以不認定。對我來講,他(王子慶)私刻順馳公司的章是加重他的責任的,應該要認定的。”
在與《證券市場周刊》記者交談中,江律師還從辦公室書柜中翻出一本《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其中第七十四條規定:訴訟過程中,當事人在起訴狀、答辯狀、陳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詞中承認的對己方不利的事實和認可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予以確認,但當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的除外。
江律師說,“王子慶就是己方當事人。”
除此之外,吳萍所做《調查詢問筆錄》也能佐證王子慶部分證言。但是,該《調查詢問筆錄》在湖北省高院判決書中卻沒有出現。“不知道為什么,他們(法院)提都沒提。”順馳公司負責人如是說。
下篇:
唯一出路是“逃離”湖北?
據《證券市場周刊》記者拿到的落款日期為2014年10月18日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本院認為,順馳公司的再審申請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二項、第六項規定的情形……指令湖北省高院再審本案;再審期間,中止原判決的執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規定,當事人的申請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其中第二項、第六項規定分別為: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的;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
順馳公司負責人還提到,閔律師(順馳公司二審代理律師)看見了最高院指導意見函,其中一條核心意見大意為:(湖北省高院應當)查證此房屋買賣行為是否真實。
上述不愿具名的荊州當地律師表示,“實際上,最高人民法院說的已經很直白了,如果認為買賣關系成立的話,他沒必要下這個東西。”
另外,一位荊州律師在了解該案件后表示,“我覺得這個案子應該屬于個人之間的民間借貸,這個商品房的買賣合同是不成立的,黃正昕應該找的是王子慶,退一步說還應該找誰,應該去找中博公司,和順馳公司沒有關系。”
當《證券市場周刊》記者問上述律師這個判決出來后給你的感覺是什么?該律師言道,“很蹊蹺,這個案子并不復雜,但后面的太復雜了。”
“現在黃正昕在申請執行,查封了我們的三十多套房產了。我們現在正在推動最高院提審,這個事情的結果只能是逃離湖北省,唯一的方法就是最高院提審。”路勁基建的法務頗顯無奈。江律師也表示,“(順馳公司)將繼續走申訴的這條途徑,希望最高人民法院提審,再依法作出一個客觀的、公正的(判決)。”
上述律師則提議道,“如果走正常的法律流程的話,(順馳公司)應該去最高檢抗訴。”
對于上述購房合同糾紛案件,《證券市場周刊》還將持續關注。
番外篇:
記者采訪手記
8月11日,《證券市場周刊》記者先是來到湖北省荊州市,給黃正昕代理律師袁良明發送短信,希望就上述購房合同糾紛案件相關疑問面訪對方,但是對方一直沒有回復。
時隔一天,《證券市場周刊》記者再次打電話聯系袁良明,其表示:“昨天你發信息以后,我和黃正昕商量了,她沒給我授權(接受采訪),所以案件的相關信息不方便跟你說。”同日,《證券市場周刊》記者先后撥打黃正昕兩個手機號,但都是無人接聽,隨后發送短信希望就案件疑問能和黃正昕當面溝通,一直未收到回復。
在8月12日,《證券市場周刊》記者還電話聯系了此案一審重審的審判長陳時中,希望就上述購房合同糾紛相關疑問采訪陳時中,陳時中表示,“我不接受采訪,必須(荊州市中院)政治部的同意。”
當天下午,《證券市場周刊》記者前往位于荊州市學院路的荊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辦公地址,在門衛指引下來到荊州市中院訴訟服務大廳,在“判后答疑”辦公窗口說明來意后,請值班人員聯系政治部,此值班員工說道,“省高院下發通知函,我們才接受媒體采訪。”
同日,《證券市場周刊》記者還電話聯系了此案二審的審判長張樂喜,張樂喜也表示:“采訪問題你和我們宣傳處聯系。”
隨后,本刊記者趕往位于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公正路9號的湖北省高院信訪接待中心,值班法官說,“(采訪)你和(省高院)政治部或者宣傳部聯系。”本刊記者通過省高院總機轉政治部,政治部工作人員表示:“接受采訪這一塊是宣傳處負責。”
在信訪接待中心,一位員工在看到記者介紹信等證明文件后,也聯系了宣傳部,但“電話沒有人接”。
8月12日,《證券市場周刊》記者在多次撥打省高院宣傳處沒有人接聽的情況下,總機幫助轉接至宣傳處內勤,該工作人員說,“我給你個號碼(尾號為“0426”的座機),你找一下我們宣傳處處長。”
隨后幾天內,《證券市場周刊》記者十數次撥打上述員工所說的宣傳處處長電話,但電話一直無人接聽。直到8月15日,該電話才有人接聽,《證券市場周刊》記者剛剛表示希望就一個合同糾紛案件采訪一下省高院,還未說完對方就掛斷電話。第二次打通后,對方問,“你找誰?”當《證券市場周刊》記者詢問“您是省高院宣傳處處長嗎?”對方表示,“你打錯了。”隨即掛斷電話。
但是,《證券市場周刊》記者再次撥打省高院總機詢問上述尾號“0426”座機是否為省高院宣傳處處長,接線員表示,“他是不是處長我不清楚,我這邊查得到這個號碼是宣傳處的。”
8月15日,《證券市場周刊》記者再次撥打黃正昕電話,在電話鈴聲響一次之后,即被掛斷。
回北京后,《證券市場周刊》記者還將相關問題分別快遞至荊州市中院和湖北省高院,但截至發稿仍未收到任何回復。
- 上一篇:先鋒新材豪賭澳洲乳業 2016/9/28
- 下一篇:城地股份身陷負增長“困境” 2016/9/26